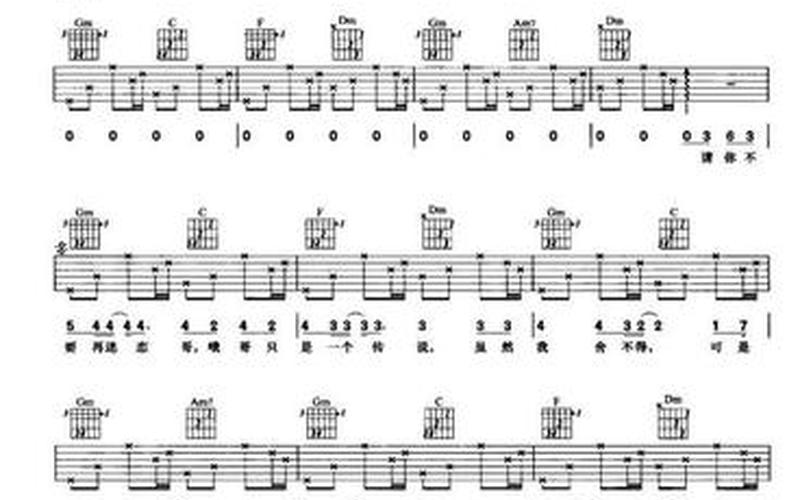韩非子是怎么死的啊?
韩非,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,先秦“法”、“木”、“势”学说的集大成者,其学说以政治哲学最为突出,他鼓吹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,对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公元前323年,韩非死于秦国。有关他的死因,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,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。 据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记载: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,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。他有些口吃,不善讲话,但很会写文章,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。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。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,只得退而著书立说,以阐明其思想。他的著作传到秦国,秦王读后大为钦佩,说:“寡人得见此人,与之游,死不恨矣!”李斯告诉秦王,这是他同学韩非所作,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,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。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,但还没有任用他,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,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。不久在狱中服毒自杀,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。此外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也记载“韩非使秦,秦用李斯谋,留非,非死云阳”。按司马迁的意思,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。 但是,在西汉刘向编写的《战国策》中,却有另一种说法。《秦策第五·四国为一特以攻秦》中讲:楚、燕、代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,秦王名大臣商议,姚贾自愿出使四国,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,回秦后得到重赏。韩非对此颇为不满,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。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,是“以王之权,国之宜,外自交于诸侯”;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,说他是“世监门子,梁之大盗,赵之逐臣”,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“厉群臣”的。秦王召姚贾质问,姚贾对答如流。说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利益考虑,如果是“自交”,他又何必回秦国;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,并列举姜太公、管仲、百里奚等名人为例,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“明主”。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,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,从这里看,韩非似又是咎由自取,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。 目前,学术界对韩非的死因,持《史记》说的居多,但也有不同看法的,大致归纳为下列几种意见: 一种意见认为: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、姚贾有关,但关键因素则在于秦王的多疑。《史记》和《战国策》的记载实际不矛盾,前者讲政治原因,后者谈个人原因,决定者则是秦王。秦王为人“少思而虎狼心,”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,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。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,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,不论学问多好,也没有存在的价值。囚禁韩非出自他的本意,杀其人而用其学说,正符合这个统治者的性格。 另一种意见则以为: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,并非李斯的嫉妒陷害。战国后期,势力强盛,秦欲扩张,韩首当其冲,对此“韩王患之,与韩非谋弱秦。”韩国的“弱秦”计划,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。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,以兴修水利来消耗秦之国力,但此事不久即败露,且修建的“郑国渠”不仅没有“弱秦”,反而使秦更趋富强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韩非亲自出马使秦以“存韩”,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并破坏姚贾的出使,李斯作为秦臣与韩非展开斗争,谈不上什么嫉妒。如果李斯是嫉妒,他又何必在秦王面前举荐韩非,而且韩非死后,李斯还是多次提及“韩非子言”。嫉妒之说是司马迁的个人偏见所致。 更有人认为: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,为“存韩”而死,实际上并不然。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,换言之就是政客。韩非到泰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,要说嫉妒之心两人皆有,两人钩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。韩非子怎么死的?韩非子得罪了谁?
韩非子是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、哲学家,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,被称为最深得老子思想精髓的二人之一。韩非子和秦国丞相李斯是同窗,但两人在政见上却有分歧,当时李斯认为应该灭韩,韩非子觉得要存韩。李斯知道韩非子的能力,担心秦王嬴政会听信韩非子的计谋,所以故意在秦王面前说了很多他的坏话,导致韩非子被擒入狱。韩非子最后也是死的挺冤的,秦王本想赦免与他,却晚了一步。我们知道,李斯与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,两人都是不世出的天才,而人们都认为韩非要略胜李斯一筹。而这也让人们觉得韩非的死与李斯有着某种关系,这是最为流传的一种说法。
另一种说法则是认为韩非说姚贾的坏话,结果害人不成,反倒赔了自己的性命。我们来分别看一下这两种说法的合理性与否。
韩非所在的韩国是七国中最弱小的国家,当时的韩王不思进取,不敢任用韩非,怕被其夺去王位,于是,韩非满腔抱负无处伸展,很是郁闷,写下了《孤愤》,《说难》等篇章。
这些文章韩王不重视,却被嬴政看到了,他手不释卷,日夕揣摩,看到精彩处就忍不住击节赞赏,渐渐地爱屋及乌,对韩非这个人起了兴趣。于是,他发动了对韩国的战争,只是为了让韩非到秦国去,因一个人而发动一场战争,由此可见韩非的魅力。
韩非果然没有让嬴政失望,他的所思所想与嬴政不谋而合,而这,却引起了李斯的妒忌,他苦心经营数十年,才在嬴政身边有了一席之地,而韩非仅凭几篇文章,几许言语,竟能让秦王如此?他怕自己再不行动,以后就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。
于是,他向秦王进言,说韩非身在秦国心在韩,不会为秦国所用,不及早杀之,必为后患。就这样,秦王将韩非下狱,李斯趁机除掉了韩非。
另一个说法是,韩非与姚贾交恶,于是向秦王说他的坏话,可是姚贾显然比口吃的韩非更加能说会道,于是让秦王相信了他的无辜,而韩非反因构陷不成而为秦王所弃,最终身败名裂。
关于韩非之死,恐怕根源还是在他自己身上,胸藏百万雄兵,徒有高等智慧,却无高等的情商,在战国这种乱世当中,确实是难以生存下来的。
下面分享相关内容的知识扩展:
《韩非子·六反第四十六》译文与赏析
六反第四十六
【题解】
本文从功利观点出发,指出社会上分别存在着六种“奸伪无益”之民和“耕战有益”之民,前者应受到诛罚却得到了称誉和礼敬,后者应得到奖赏却受到了轻视和贬抑,这就是“六反”。据此,文章又进一步反对仁爱、轻刑、足民,提倡君主以威严治国、以信赏必罚劝禁。
【原文】
畏死远难,降北之民也,而世尊之曰“贵生之士”[1]。学道立方,离法之民也,而世尊之曰“文学之士”[2]。游居厚养,牟食之民也,而世尊之曰“有能之士”[3]。语曲牟知,伪诈之民也,而世尊之曰“辩智之士”[4]。行剑攻杀,暴憿之民也,而世尊之曰“磏勇之士”[5]。活贼匿奸,当死之民也,而世尊之曰“任誉之士”。此六民者,世之所誉也。赴险殉诚,死节之民,而世少之曰“失计之民”也。寡闻从令,全法之民也,而世少之曰“朴陋之民”也。力作而食,生利之民也,而世少之曰“寡能之民”也。嘉厚纯粹,整谷之民也,而世少之曰“愚戆之民”也。重命畏事,尊上之民也,而世少之曰“怯慑之民”也。挫贼遏奸,明上之民也,而世少之曰“謟谗之民”也。此六民者,世之所毁也。奸伪无益之民六,而世誉之如彼;耕战有益之民六,而世毁之如此;此之谓“六反”。布衣循私利而誉之,世主听虚声而礼之,礼之所在,利必加焉。百姓循私害而訾之,世主壅于俗而贱之,贱之所在,害必加焉[6]。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,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,索国之富强,不可得也。
【注释】
[1]难:危难。降北:投降败逃。[2]方:方术,学说。[3]牟食之民:指依靠游说混饭吃的人。牟,贪取,侵夺。[4]语曲:诡辩。牟知:从事于玩弄智巧。牟:通“务”。知:通“智”。[5]暴憿之民:凶暴而冒险的人。憿,通“侥”,侥幸。磏:(lián)磨刀石,引申为有锋芒、有棱角。[6]訾:诋毁。
【译文】
贪生怕死逃避危难,是投降败逃的人,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“重视生命的人”。学道术立方术,是背离法制的人,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“有学问的人”。到处游说得到丰厚供养,是依靠游说混饭吃的人,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“有才能的人”。空谈诡辩玩弄智巧,是虚伪诡诈的人,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“雄辩智慧的人”。用剑行刺攻击杀人,是凶暴而冒险的人,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“有锋芒勇敢的斗士”。救活贼子藏匿坏人,是应当判处死刑的罪犯,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“讲名声有信誉的人”。这六种人,是社会上所称赞的。为国赴险忠诚献身,是为节操而牺牲的人,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“不会算计的傻瓜”。见闻少顺从命令,是守法的良民,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“朴实丑陋的人”。努力劳作自食其力,是创造财富的人,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“缺少才能的人”。善良厚道单纯质朴,是正派善良的人,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“愚昧刚愎的人”。重视命令谨慎办事,是尊重君主的人,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“胆小怕事的人”。挫败乱贼遏制奸邪,是使君主明白的人,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“奉承说别人坏话的人”。这六种人,是社会上所诋毁的人。奸邪诡诈无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,而社会上竟像那样来称赞他们;耕地作战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,而社会上却如此诋毁他们;这就叫做“六种反常”。布衣百姓考虑到自己的私利而称赞那些无益于国家的人,当代君主听到这些虚名就礼遇他们,礼遇他们,必定给予他们好处。布衣百姓考虑到对自己有害而诋毁那些有益于国家的人,当代君主被世俗偏见所蒙蔽而鄙视他们,被鄙视,必定会受害。所以名誉奖赏给了那些谋私作恶应当惩罚的人,而诋毁刑罚却加罪于那些为国家做好事应该奖赏的人,要想求得国家的富强,是不可能的。
【原文】
古者有谚曰:“为政犹沐也,虽有弃发,必为之。”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,不知权者也。夫弹痤者痛,饮药者苦,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,则身不活,病不已矣[1]。今上下之接,无子父之泽,而欲以行义禁下,则交必有郄矣[2]。且父母之于子也,产男则相贺,产女则杀之。此俱出父母之怀衽,然男子受贺,女子杀之者,虑其后便,计之长利也[3]。故父母之于子也,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,而况无父子之泽乎?今学者之说人主也,皆去求利之心,出相爱之道,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,此不熟于论恩,诈而诬也,故明主不受也。圣人之治也,审于法禁,法禁明着,则官法;必于赏罚,赏罚不阿, *** 用。官治则国富,国富则兵强,而霸王之业成矣。霸王者,人主之大利也。人主挟大利以听治,故其任官者当能,其赏罚无私。使士民明焉,尽力致死,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,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。富贵者,人臣之大利也。人臣挟大利以从事,故其行危至死,其力尽而不望。此谓君不仁,臣不忠,则不可以霸王矣。
【注释】
[1]弹痤:(tán)用石针割刺痈。痤:痈。[2]郄:(xì)同“郤”,也作“隙”,空隙、裂缝。[3]怀衽:怀抱。衽,衣襟。
【译文】
古代有谚语说:“处理政事就好比洗头,虽然会掉一些头发,但一定会洗头。”舍不得掉头发的耗费而忘记洗头能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,就是不懂得权衡利弊得失的人。用针刺痈会疼痛,喝药会口苦,因为痛苦的缘故而不刺痈喝药,那么自己就不能活命了,病就治不好了。如今君臣之间的交往关系,没有父子之间的恩惠,而想用施行仁义的措施来禁控臣下,那么君臣的交往关系必定会有裂缝。况且父母亲对于子女,生了儿子就去祝贺,生了女儿就杀死。子女都是父母所生,但生了儿子就祝贺,生了女儿就杀死,这是因为父母亲考虑到他们对自己今后的利益,计算长远的利益。所以父母亲对于子女,尚且用计算对自己是否有利的心思去对待他们,更何况是没有父子之恩惠的人呢?如今学者游说君主,都叫君主去掉求利的思想,从相爱的原则出发,这是要求君主对臣民的爱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,这是谈论恩惠的无知之谈,是一种欺骗和杜撰,所以英明的君主是不接受的。圣明的人治理国家,首先审查法律禁令,法律禁令明白了,那么官府就能依法治理政务;其次坚决地实行赏罚,赏罚不偏私,那么民众就能被使用。民众能被使用官府得到治理,那么国家就能富裕,国家富裕那么兵力就会强盛,而称霸称王的事业就能成就。称王称霸,是君主更大的利益。君主为了获取大利益来治理国家,所以任用官吏的时候要求才能相当,赏罚时没有偏私。使士人民众都明白此道理,尽力拼命,那么就能建立功绩获得爵位俸禄,爵位俸禄只要得到了而富贵的事业也就成就了。富贵,是臣子的更大利益。臣子为了获取大利益来做事,所以拼死应对危难,即使尽全力死了也无怨恨。这就是说,君主不施仁爱,臣下不效忠诚,那么就不可能称王称霸了。
【原文】
夫奸,必知则备,必诛则止;不知则肆,不诛则行。夫陈轻货于幽隐,虽曾、史可疑也;悬百金于市,虽大盗不取也。不知,则曾、史可疑于幽隐;必知,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。故明主之治国也,众其守而重其罪,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。母之爱子也倍父,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;吏之于民无爱,令之行于民也万父。母积爱而令穷,吏威严而民听从,严爱之策亦可决矣。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,动作则欲其安利也,行身则欲其远罪也。君上之于民也,有难则用其死,安平则尽其力。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,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。明主知之,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。故母厚爱处,子多败,推爱也;父薄爱教笞,子多善,用严也。
【译文】
奸邪的人,必定被别人知道才会有戒备,必定被别人惩罚才会停止;不被别人知道就会放肆,不受到惩罚就会横行。如果把轻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货物陈放在幽暗隐蔽的地方,即使是曾参、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也可以被怀疑;把百金悬挂在市场上,虽然是大盗也不敢去取。不被知道,那么曾参、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也可以被怀疑;必定被知道,那么大盗也不敢偷取悬挂在市场上的百斤。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,防范措施多而惩罚重,使民众因法令受到约束而不是凭品行的廉洁停止作恶。母亲对子女的爱胜过父亲的数倍,但父亲的命令在子女那里得到执行却是母亲的十倍;差役对民众没有什么仁爱,其命令在民众那里得到执行却是父亲的万倍。母亲积聚仁爱而命令却行不通,差役运用威严而民众就听从,以此到底采用威严还是仁爱的策略,也就能决断了。况且父母亲所要求子女的,希望他们在行动方面安全有利,希望他们在立身处世方面远离罪过。君主对于民众,国家有灾难就用他们拼死卖命,安定太平时就使他们尽力生产。父母亲怀着深厚的爱关切子女安全利益仁子女却不听从,君主不用仁爱和利益的要求民众卖命而命令却能执行。英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,所以不培养恩爱之心而增强威严之势。所以母亲以深厚的爱对待子女,子女多半品行变坏,这是因为推行了仁爱;父亲淡泊仁爱用竹板子抽打管教子女,子女多半品行善良,这是因为使用了威严。
【原文】
今家人之治产也,相忍以饥寒,相强以劳苦,虽犯军旅之难,饥馑之患,温衣美食者,必是家也;相怜以衣食,相惠以佚乐,天饥岁荒,嫁妻卖子者,必是家也。故法之为道,前苦而长利;仁之为道,偷乐而后穷。圣人权其轻重,出其大利,故用法之相忍,而弃仁人之相怜也。学者之言皆曰“轻刑”,此乱亡之术也。凡赏罚之必者,劝禁也。赏厚,则所欲之得也疾;罚重,则所恶之禁也急。夫欲利者必恶害,害者,利之反也。反于所欲,焉得无恶?欲治者必恶乱,乱者,治之反也。是故欲治甚者,其赏必厚矣;其恶乱甚者,其罚必重矣。今取于轻刑者,其恶乱不甚也,其欲治又不甚也。此非特无术也,又乃无行。是故决贤、不肖、愚、知之美,在赏罚之轻重。且夫重刑者,非为罪人也。明主之法,揆也[1]。治贼,非治所揆也;所揆也者,是治死人也。刑盗,非治所刑也;治所刑也者,是治胥靡也[2]。故曰: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,此所以为治也。重罚者,盗贼也;而悼惧者,良民也。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名!若夫厚赏者,非独赏功也,又劝一国。受赏者甘利,未赏者慕业,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,欲治者何疑于厚赏!今不知治者皆曰:“重刑伤民,轻刑可以止奸,何必于重哉?”此不察于治者也。夫以重止者,未必以轻止也;以轻止者,必以重止矣。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,奸尽止,则此奚伤于民也?所谓重刑者,奸之所利者细,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。民不以小利加大罪,故奸必止者也。所谓轻刑者,奸之所利者大,上之所加焉者小也。民慕其利而傲其罪,故奸不止也。故先圣有谚曰:“不踬于山,而踬于垤[3]。”山者大,故人顺之;垤微小,故人易之也。今轻刑罚,民必易之。犯而不诛,是驱国而弃之也;犯而诛之,是为民设陷也。是故轻罪者,民之垤也。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,非乱国也,则设民陷也,此则可谓伤民矣!
【注释】
[1]揆:(kuí)大致估量现实状况。[2]胥靡:犯轻罪被罚苦役的人。[3]踬:(zhì)绊倒。垤:(dié)小土堆。
【译文】
如今一般人家治理产业时,用忍饥寒来相互鼓励,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监督,虽然遭到战争的祸乱,荒年的灾患,还能够穿暖吃饱,必定就是这种家庭了;用丰衣美食来相互怜爱,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,如果碰上天灾荒年,卖妻卖子的,必定是这种家庭了。所以用法治作为治国策略,开始吃点苦而有长远利益;用仁爱作为治国策略,暂时得到欢乐但终究要遭受穷苦。圣人权衡这其中的轻重,从长远利益出发,所以用法治使民众能忍受管束,而废除仁爱对民众的怜爱。学者们的意见都说“减轻刑罚”,这是使国家混乱灭亡的措施。赏罚决断,就是为了勉励立功禁止犯罪。奖赏丰厚,那么想要的就迅速得到;惩罚严重,那么所厌恶的就会很快得到禁止。想要得到利益的人必定厌恶受害,受害,就是利益的反面。违反自己的欲望,怎么能不厌恶呢?想要治理的人必定厌恶混乱,混乱,是治理的反面。因此想把国家治理好的人,他的奖赏必定丰厚;那非常厌恶混乱的人,他的惩罚必定很重。如今采取减轻刑罚的人,他不是很厌恶混乱,所以他也不是很想治理好国家。这不仅是没有治国的法术,而且没有治国的理论。因此判断人们的贤能、不贤能、愚蠢、智慧的标准,在于赏罚的轻重。况且实施重刑,并不是要惩罚某一个人。英明君主的法制,是估量所有人德行的准则。治罪贼子,并不是治罪贼子一个人;如果治罪贼子一个人,那仅仅是治罪了一个死囚。刑罚大盗,并不只惩罚大盗一个人;如果只是惩罚大盗一个人,那仅仅惩罚了一个囚犯。所以说:对一个坏人的惩罚而可以禁止全国的坏人,这才是惩罚的目的。受重罚的,是盗贼;而感到恐惧的,是善良的民众。想要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对重刑的作用还有什么可怀疑呢!至于厚赏,并不只是为了奖赏有功绩的人,而也是为了劝勉全国的人。受到奖赏的人乐于得利,没有受到奖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,这是酬劳了一个人的功劳而劝勉了全国的民众,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!如今不知道治国 *** 的人都说:“严厉的刑罚伤害民众,轻刑就可以禁止奸邪了,何必一定要加重刑罚呢?”这是没有仔细考察治国 *** 。用重刑能制止的,用轻刑不一定能制止;用轻刑能制止的,用重刑就一定能制止。因此君主设置重刑,奸邪全部能被禁止,奸邪全部禁止了,那么这重刑对于民众又有什么伤害呢?所谓的重刑,是指坏人得到的好处很小,而君主加在他们头上的惩罚很重。民众决不会为了很小的好处而甘愿被重罚,所以坏人就一定会被禁止。所谓的轻刑,就是指坏人得到的好处很多,君主加到他们头上的惩罚很轻。民众羡慕做坏事的大利益而轻视那很轻的惩罚,所以坏人就禁止不了。所以先圣人有句谚语说:“人不会被高山绊倒,而会被小土堆绊倒。”山高大,所以人们就谨慎对待它;小土堆很小,所以人们就忽视它。如今刑罚很轻,民众必定忽视它。违反了法律而不惩处,就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;违反了法律而惩处,就等于给民众设置陷阱。因此轻微的处罚,相当于民众的小土堆。因此把轻刑作为治理国家的策略,不是扰乱国家,就是给民众设置陷阱了,这才称作伤害民众啊!
【原文】
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,不察当世之实事,曰:“上不爱民,赋敛常重,则用不足而下恐上,故天下大乱[1]。”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,虽轻刑罚,可以治也。此言不然矣。凡人之取重赏罚,固已足之之后也;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,然而轻刑,犹之乱也。夫当家之爱子,财货足用,货财足用则轻用,轻用则侈泰。亲爱之则不忍,不忍则骄恣。侈泰则家贫,骄恣则行暴。此虽财用足而爱厚,轻利之患也。凡人之生也,财用足则隳于用力,上懦则肆于为非。财用足而力作者,神农也;上治懦而行修者,曾、史也,夫民之不及神农、曾、史亦明矣[2]。老聃有言曰:“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。”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,老聃也。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,是以民为皆如老聃。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,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。君人者虽足民,不能足使为君天子,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,则虽足民,何可以为治也?故明主之治国也,适其时事以致财物,论其税赋以均贫富,厚其爵禄以尽贤能,重其刑罚以禁奸邪,使民以力得富,以事致贵,以过受罪,以功致赏,而不念慈惠之赐,此帝王之政也。
【注释】
[1]道:称说。书策:典籍。策:通“册”。赋敛:征收的赋税。[2]神农:传说中发明原始农耕的人。曾、史:曾参、史鱼。
【译文】
如今学者们都称说典籍中歌功颂德的空话,不明了当代的实际情况,都说:“君主不爱民,征收的赋税一直沉重,导致财物不够用而民众怨恨君主,所以天下大乱。”这是认为使民众财物足用就是对民众的仁爱,虽然减轻刑罚,也可以治理好的。这种说法并不对。凡是受到重罚的人,原本就是在他富足之后犯罪的;虽然使民众财物富足之后再去深爱他们,然而减轻刑罚,还是会混乱的。比如当家长的溺爱子女,子女的财物足够使用,财物足够使用那么就会轻易乱用,轻易乱用就会浪费奢侈。家长溺爱他们就不忍心约束他们,不忍心约束他们那么就会使他们骄横放纵。浪费奢侈就会使家庭贫困,骄横放纵就会使他们行为暴虐。这就是财物使用富足,爱得深厚,采用轻刑的祸患。大凡人的本性,财物富足之后就会懒惰于劳动,君主管治软弱就会放肆地为非作歹。财物富足之后仍然尽力劳作的,是神农那样的人;君主管治软弱而仍然尽力修行的,是曾参、史鱼那样的人,而民众比不上神农、曾参、史鱼那是很明显的。老聃有句话说:“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,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。”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而在满足之后不再谋求私利的人,只有老聃。如今以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,这是把民众都当作老聃了。所以夏桀高贵地处在天子之位上还不满足自己的尊贵,富有得拥有天下还不满足于他的珍宝。统治人民的君主虽然能满足民众的财物,也不能使他们当上天子,而夏桀未必认为当天子是满足的事,那么虽然使人民富足,又怎么能把这作为治国的策略呢?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,适应天时来获得财物,评定赋税使贫富平均分担,加重爵位俸禄来使人们尽心尽力,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,使民众通过卖力而得到财富,通过给国家办事而得到尊贵,因过错而受到惩罚,因立功而得到奖赏,而不惦记君主仁慈恩惠的赏赐,这才是帝王治理国家的 *** 。
【原文】
人皆寐,则盲者不知;皆嘿,则喑者不知[1]。觉而使之视,问而使之对,则喑盲者穷矣。不听其言也,则无术者不知;不任其身也,则不肖者不知。听其言而求其当,任其身而责其功,则无术不肖者穷矣。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,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;授之以鼎俎,则罢健效矣[2]。故官职者,能士之鼎俎也,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。故无术者得于不用,不肖者得于不任。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,身不任者而自饰以为高。世主眩其辩、滥其高而尊贵之,是不须视而定明也,不待对而定辩也,喑盲者不得矣。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,观其行必求其功,然则虚旧之学不谈,矜诬之行不饰矣。
【注释】
[1]嘿:通“默”。喑:哑。[2]乌获:人名,战国秦武王时的大力士。罢:通“疲”,疲弱。
【译文】
人都睡着了,就不能知道谁是瞎子;都沉默了,就不能知道谁是哑巴。醒过来让他们看东西,提问题让他们回答,那么谁是哑巴、瞎子就都完全知道了。不听取他们的言论,就不会知道谁没有法术;不任用他们做事,就不会知道谁不贤德。听取他们的言论责求与他们的行为相当,任用他们本身要求他们处理事情的功效,那么无法术不贤能的人就完全知道了。想要得到大力士却听从他们自夸,即使是庸人与乌获也不能被识别出来;如果拿鼎俎让他们举一下,那么谁疲弱谁强健就表现出来了。所以官职,就相当于有才能之人的鼎俎,把职事交给他们干一下而愚蠢和聪明就能分辨出来了。所以没有法术的人就得不到重用,无才德的人就得不到任用。他们的言论没有被采用就自我粉饰认为自己有口才,他们本人没有被任用就自夸认为自己高明。世俗的君主迷惑于他们的口才、轻信他们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,这就是不等待他们看东西就确定他们的视力好,不等待他们回答就确定他们的口才好,谁是哑巴谁是瞎子就不能分辨了。英明的君主听取他的言论必定要求它的功用,观察他们的行为必定责求它的功效,那么陈腐空洞的学说就无人再谈了,自夸欺骗的行为就得不到掩饰了。
【评析】
六反,就是六种反常现象,应该受到惩罚的奸邪之人,却受到世俗的称赞,应该受到称赞的人,却受到世俗的诋毁。难怪有许多人心理不平衡。统治者如果受到世俗舆论的蒙蔽和影响,必然就会使赏罚失当,从而不能使国家富强。
韩非偏激的认为,君主统治不应该讲仁爱,实际上,上下级之间的仁爱关系是互相爱护的关系,只有上级爱护下级,下级也爱护上级,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。如果谁都不爱护对方,只为了自己的私利去为人处世,那么统治政权也就维持不下去了。韩非认为,只要法、罚重,那么很多人就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方式;法制严密,奸邪的行为就会被知道,被觉察,法制不严密,那么谁都值得怀疑;所以法制、法治是重中之重。这是不对的,一个国家的治理,最关键的就是了解人们的风俗习惯,并且根据各种原因,移风易俗,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。法律,只是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补充,一种外在形式的,一种条文形式的补充。
六反,讲的是六种反常现象,当然在实际生活中、实际工作中不止只有这六种反常现象,有很多反常现象都需要我们去清醒地认识、区分。不能认为这种现象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正常现象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论时代怎样发展,总是要团结互助,相互仁爱的。否则,人类也就走投无路,永远困穷了。
韩非子五蠹原文 原文讲解
1、原文:上古之世,人民少而禽兽众,人民不胜禽兽虫蛇。有圣人作,构木为巢以避群害,而民悦之,使王天下,号曰有巢氏。民食果蓏蚌蛤,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,民多疾病。有圣人作,钻燧取火以化腥臊,而民说之,使王天下,号之曰燧人氏。中古之世,天下大水,而鲧、禹决渎。近古之世,桀、纣暴乱,而汤、武征伐。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,必为鲧、禹笑矣;有决渎于殷、周之世者,必为汤、武笑矣。然则今有美尧、舜、鲧、禹、汤、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,必为新圣笑矣。是以圣人不期修古,不法常可,论世之事,因为之备。2、宋人有耕田者,田中有株,兔走触株,折颈而死,因释其耒而守株,冀复得兔。兔不可复得,而身为宋国笑。今欲以先王之政,治当世之民,皆守株之类也。
3、古者丈夫不耕,草木之实足食也;妇人不织,禽兽之皮足衣也。不事力而养足,人民少而财有余,故民不争。是以厚赏不行,重罚不用,而民自治。今人有五子不为多,子又有五子,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。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,事力劳而供养薄,故民争,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。
4、尧之王天下也,茅茨不翦,采椽不斫;粝粢之食,黎藿之羹;冬日麂裘,夏日葛衣;虽监门之服养,不亏于此矣。禹之王天下也,身执耒臿以为民先,股无完胈,胫不生毛,虽臣虏之劳,不苦于此矣。以是言之,夫古之让天子者,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,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。今之县令,一日身死,子孙累世絜驾,故人重之。是以人之于让也,轻辞古之天子,难去今之县令者,薄厚之实异也。夫山居而谷汲者,膢腊而相遗以水;泽居苦水者,买庸而决窦。故饥岁之春,幼弟不饷;穰岁之秋,疏客必食。非疏骨肉爱过客也,多少之实异也。是以古之易财,非仁也,财多也;今之争夺,非鄙也,财寡也。轻辞天子,非高也,势薄也;重争士橐,非下也,权重也。故圣人议多少、论薄厚为之政。故罚薄不为慈,诛严不为戾,称俗而行也。故事因于世,而备适于事。
5、古者文王处丰、镐之间,地方百里,行仁义而怀西戎,遂王天下。徐偃王处汉东,地方五百里,行仁义,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。荆文王恐其害己也,举兵伐徐,遂灭之。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,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,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。故曰:世异则事异。当舜之时,有苗不服,禹将伐之。舜曰:“不可。上德不厚而行武,非道也。”乃修教三年,执干戚舞,有苗乃服。共工之战,铁铦短者及乎敌,铠甲不坚者伤乎体。是干戚用于古,不用于今也。故曰:事异则备变。上古竞于道德,中世逐于智谋,当今争于气力。齐将攻鲁,鲁使子贡说之。齐人曰:“子言非不辩也,吾所欲者土地也,非斯言所谓也。”遂举兵伐鲁,去门十里以为界。故偃王仁义而徐亡,子贡辩智而鲁削。以是言之,夫仁义辩智,非所以持国也。去偃王之仁,息子贡之智,循徐、鲁之力,使敌万乘,则齐、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。
6、夫古今异俗,新故异备。如欲以宽缓之政,治急世之民,犹无辔策而御马,此不知之患也。今儒、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,则视民如父母。何以明其然也?曰:“司寇行刑,君为之不举乐;闻死刑之报,君为流涕。”此所举先王也。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,推是言之,是无乱父子也。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,皆见爱而未必治也,虽厚爱矣,奚遽不乱?今先王之爱民,不过父母之爱子,子未必不乱也, *** 奚遽治哉?且夫以法行刑,而君为之流涕,此以效仁,非以为治也。夫垂泣不欲刑者,仁也;然而不可不刑者,法也。先王胜其法,不听其泣,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。
7、且民者固服于势,寡能怀于义。仲尼,天下圣人也,修行明道以游海内,海内说其仁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。盖贵仁者寡,能义者难也。故以天下之大,而为服役者七十人,而仁义者一人。鲁哀公,下主也,南面君国,境内之民莫敢不臣。民者固服于势,诚易以服人,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。仲尼非怀其义,服其势也。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,乘势则哀公臣仲尼。今学者之说人主也,不乘必胜之势,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,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,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,此必不得之数也。
8、今有不才之子,父母怒之弗为改,乡人谯之弗为动,师长教之弗为变。夫以父母之爱、乡人之行、师长之智,三美加焉,而终不动,其胫毛不改。州部之吏,操官兵,推公法,而求索奸人,然后恐惧,变其节,易其行矣。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,必待州部之严刑者,民固骄于爱、听于威矣。故十仞之城,楼季弗能逾者,峭也;千仞之山,跛牂易牧者,夷也。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。布帛寻常,庸人不释;铄金百溢,盗跖不掇。不必害,则不释寻常;必害手,则不掇百溢。故明主必其诛也。是以赏莫如厚而信,使民利之;罚莫如重而必,使民畏之;法莫如一而固,使民知之。故主施赏不迁,行诛无赦,誉辅其赏,毁随其罚,则贤、不肖俱尽其力矣。
9、今则不然。其有功也爵之,而卑其士官也;以其耕作也赏之,而少其家业也;以其不收也外之,而高其轻世也;以其犯禁罪之,而多其有勇也。毁誉、赏罚之所加者,相与悖缪也,故法禁坏而民愈乱。今兄弟被侵,必攻者,廉也;知友辱,随仇者,贞也。廉贞之行成,而君上之法犯矣。人主尊贞廉之行,而忘犯禁之罪,故民程于勇,而吏不能胜也。不事力而衣食,谓之能;不战功而尊,则谓之贤。贤能之行成,而兵弱而地荒矣。人主说贤能之行,而忘兵弱地荒之祸,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。
10、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,而人主兼礼之,此所以乱也。夫离法者罪,而诸先王以文学取1;犯禁者诛,而群侠以私剑养。故法之所非,君之所取;吏之所诛,上之所养也。法、趣、上、下,四相反也,而无所定,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。故行仁义者非所誉,誉之则害功;文学者非所用,用之则乱法。楚之有直躬,其父窃羊,而谒之吏。令尹曰:“杀之!”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,报而罪之。以是观之,夫君之直臣,父之暴子也。鲁人从君战,三战三北。仲尼问其故,对曰:“吾有老父,身死莫之养也。”仲尼以为孝,举而上之。以是观之,夫父之孝子,君之背臣也。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,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。上下之利,若是其异也,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,而求致社稷之福,必不几矣。
11、古者苍颉之作书也,自环者谓之私,背私谓之公,公私之相背也,乃苍颉固以知之矣。今以为同利者,不察之患也,然则为匹夫计者,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。行义修则见信,见信则受事;文学习则为明师,为明师则显荣:此匹夫之美也。然则无功而受事,无爵而显荣,为有政如此,则国必乱,主必危矣。故不相容之事,不两立也。斩敌者受赏,而高慈惠之行;拔城者受爵禄,而信廉爱之说;坚甲厉兵以备难,而美荐绅之饰;富国以农,距敌恃卒,而贵文学之士;废敬上畏法之民,而养游侠私剑之属。举行如此,治强不可得也。国平养儒侠,难至用介士,所利非所用,所用非所利。是故服事者简其业,而于游学者日众,是世之所以乱也。
12、且世之所谓贤者,贞信之行也;所谓智者,微妙之言也。微妙之言,上智之所难知也。今为众人法,而以上智之所难知, *** 无从识之矣。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,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。夫治世之事,急者不得,则缓者非所务也。今所治之政,民间之事,夫妇所明知者不用,而慕上知之论,则其于治反矣。故微妙之言,非民务也。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,必将贵不欺之士;不欺之士者,亦无不欺之术也。布衣相与交,无富厚以相利,无威势以相惧也,故求不欺之士。今人主处制人之势,有一国之厚,重赏严诛,得操其柄,以修明术之所烛,虽有田常、子罕之臣,不敢欺也,奚待于不欺之士?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,而境内之官以百数,必任贞信之士,则人不足官。人不足官,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。故明主之道,一法而不求智,固术而不慕信,故法不败,而群官无奸诈矣。
千古奇冤——韩非子被冤杀,说出来你都不信,全完是他咎由自取
韩非子,战国后期韩国的贵族公子,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,法学学派的代表人物。秦王嬴政对他是求贤若渴,赞誉有加,但是后来韩非子却冤死在了秦国,关于他的死因一直是个千古之谜,那么 历史 上韩非子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呢?
战国后期,战国七雄争霸,秦国一支独大,其综合国力已远超其他六国。而与秦国接壤的韩国更是被秦国打压的没有战略空间了,越来越弱小和贫穷了。
韩非子从小都爱好刑名法术学问,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,而韩非子有口吃的缺陷,不善于言谈,却爱好著书立说。
他看到自己的祖国韩国渐渐衰弱,心痛不已,屡次上书规劝韩王,希望韩王采纳他的意见,改变韩国日薄西山的现状,但是韩王没有听取他的建议。不得已韩非子只能放弃,开始了他的写书之路。
当时韩非子痛恨君王治理国家不用修明法治,不能凭借君王掌握的权势来驾驭臣子,没有任用贤能之士而富国强兵,他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,将商鞅的“法”、申不害的“术”和慎到的“势”集于一身,将老子的辩证法和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融为一体,写了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内外储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等十余万字的著作。
此时的秦国为了统一天下,招贤纳士,秦王嬴政也求贤若渴。当韩非子的著作传到了秦国,嬴政见到了《孤愤》这些书,长吁短叹到:“要是能见到韩非子,并能和他交往,寡人就是死了也没有遗憾了”。李斯对嬴政说到:“韩非子是我的同门师兄弟,而且他比我更加有才能”。
为了能得到韩非子,秦王嬴政决定使用暴力,他下令立即出兵攻打韩国。因秦国攻韩,等到前线形势吃紧,不得已韩王在危急关头召见韩非子,派遣他出使秦国。
到了秦国,秦王嬴政很是喜欢他,非常看重韩非子的法家学说,韩非子成了嬴政的座上宾。
秦国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,都是采用稳扎稳打,一步一个脚印,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消灭,而为了对付强大的秦国,其他六国就必须联合起来,共同对抗秦国。
姚贾——韩非子的生死冤家
姚贾,魏国人,出身“世监门子”,其父是看管城门的监门卒。虽然他出生低微,可是经历却相当传奇,后来被韩非子称其为“梁之大盗,赵之逐臣”。在赵国,姚贾被赵王全权委托,联合楚国、韩国、魏国,合众攻秦,而后秦国使用连横之计,破坏四国联盟,姚贾也被赵国逐出其境。此处不留爷,自由留爷处,姚贾跑到秦国,得到了嬴政的礼遇和赞赏。
虽然姚贾被撵走了,但是四国联军并没有瓦解,俗话说双拳不敌四手,这几个小国聚在一起,嬴政也寝食难安,于是嬴政召集群臣宾客,商议怎么退敌。这个时候姚贾挺身而出,说他愿意出使各国,破坏他们的合纵之计,嬴政一听很是高兴,说如果解决了此事,我们便可安枕无忧了。
嬴政给姚贾“资车百乘,金千斤,衣以其衣冠,舞以其剑”。这种待遇,有秦一代,并不多见。出使三年,大有成绩,和四国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,进而瓦解了四国联盟,嬴政大悦,拜为上卿,封千户。
姚贾此行却触碰了韩非子的“个人利益”,因为韩非子是韩国人,他来到秦国做事,只是想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,但是对于韩国是很有感情的。而姚贾破坏合纵,他的祖国韩国就会首先面临被灭的后果,想到这里就恨死了姚贾。
之一回合,韩非子得胜
思来想去,韩非子决定报复姚贾,向秦王嬴政告黑状,说姚贾花了大量的金钱,结交各个诸侯国,未必能让这些诸侯国亲近秦国,反而是姚贾为他自己留后路,以后在秦国呆不住了,他就可以混到其他国家去。韩非子还说姚贾这人对秦国不忠,有私心。
嬴政一听,觉得有理,非常生气,把姚贾喊来,问他话:“听说你拿着我给你的钱财,来结交诸侯国,为了自己的前程铺后路,有没有这样的事情”?
第二回合,姚贾反败为胜
姚贾一听,这是有人告黑状,想陷害与他,因为花钱结交诸侯,确实是真的,如果调查起来,这是瞒不住的。聪明的姚贾首先承认了确实有这么回事,嬴政一听急了,你怎么干这事呢?
这个时候姚贾向嬴政解释到:“我为了和诸侯搞好关系,肯定要用钱财来打通关系,我这出发点是好的,我要不用钱结交诸侯,怎么能让他们信任我呢?大王您看,曾子是个大孝子,所以天下的父母都争着想让他当儿子;伍子胥是个忠臣,所以天下君王都想让他做臣子;诸侯为什么愿意结交我呢,因为我是个忠臣,我得到大王您的信任和倚重,如果大王不信任我,哪个诸侯愿意结交我呢?这些钱财就是打通关系的润滑剂”。
秦王嬴政听了连连点头,脸上也露出了喜悦之情。接着姚贾又说到:“当年夏桀听信谗言杀死自己的大臣,商纣王听信谗言杀害忠臣良将,这两位最后国家都被人家都灭了,大王您要听信谗言,谁还敢为您尽忠呢”?
一番话说得秦王对韩非子有了想法了,以后韩非子向秦王告姚贾的黑状,秦王根本不信了。忍无可忍的姚贾为了一劳永逸,永绝后患,他就联合李斯反告韩非子的黑状。
第三回合,姚贾和李斯联手置韩非子于死地
姚贾对嬴政说:“大王,我们秦国消灭六国,一统天下是迟早的事情,而韩非子是韩国人,他一定会向着韩国,这不是个隐患吗,早晚要出事”。姚贾停下来,嬴政细想一下觉得姚贾说得有道理。接着姚贾又说到:“韩国是目前实力最弱小的,大秦灭掉韩国是最轻松的,可是韩非子却建议大王先消灭其他国家,他这不是有私心吗”?而李斯这个时候十分嫉妒韩非子的才能远在自己之上,也对韩非子落井下石,细说韩非子的种种不是。
秦王虽然很欣赏韩非子的政治主张,但是更加相信李斯,进而听信了李斯和姚贾的谗言,将韩非子关入大牢,李斯又怕嬴政到时候反悔,就用毒药害死了韩非子。
纵观韩非子的一生,他是个有大才之能人,同时他也时运不济,仕途坎坷,最终含冤致死,让后人感到甚是可惜。可是,不作死就不会死,他的死完全是他咎由自取,他如果不告黑状,也许秦国一统天下之大功非他莫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