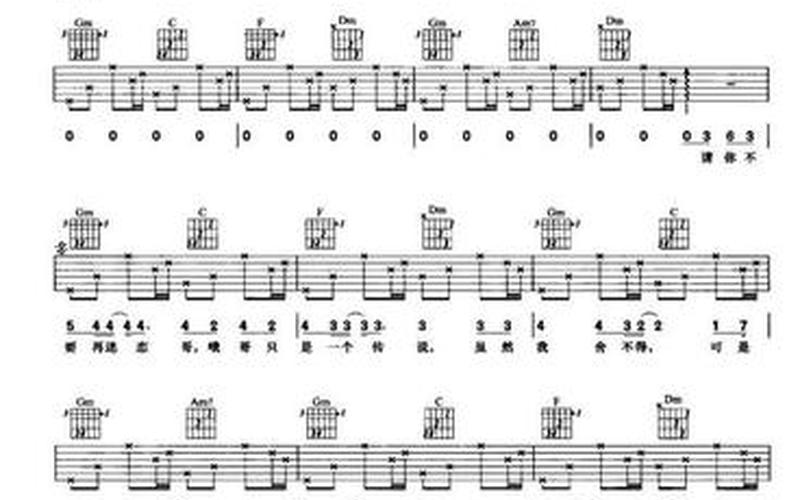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什么 那不勒斯四部曲有什么
1、埃莱娜·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《我的天才女友》《新名字的故事》《离开的,留下的》和《失踪的孩子》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,被称为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。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,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。2、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“费兰特热”,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、尖锐、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。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,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“自传性”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。2015年,埃莱娜·费兰特被《金融时报》评为“年度女性”。2016年,《时代》周刊将埃莱娜·费兰特选入“更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”。
那不勒斯四部曲什么时候写的?
1990年代。
那不勒斯四部曲,是意大利一位神秘的作家埃莱娜.费兰特写的关于两位生于贫民窟的女孩的一生的。之所以说是神秘的作家,因为作家本人是何人,是男是女均不知,其本人从未公开露面,作家姓名也只是笔名而已。
四部曲分别为《我的天才女友》、《新名字的故事》、《离开的,留下的》、《失踪的孩子》。四本书,贯穿一生。
下面分享相关内容的知识扩展:
《离开的,留下的那不勒斯四部曲-03》pdf下载在线阅读全文,求百度网盘云资源
《离开的,留下的》([意] 埃莱娜·费兰特)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VjtVT7-kjk51jh8TX2Y5bg
书名:离开的,留下的
作者:[意] 埃莱娜·费兰特
译者:陈英
豆瓣评分:8.8
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
出版年份:2017-10
页数:417
内容简介:
两个女人 50年的友谊和战争
作者简介:
埃莱娜·费兰特,目前意大利更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。埃莱娜·费兰特是一个笔名,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。
埃莱娜·费兰特1992年发表之一部长篇小说《讨厌的爱》,很快引起关注,1995年就被意大利导演马里奥·马尔托内拍摄为同名影片;此后她相继出版小说《被抛弃的日子》(2002)、《迷失的女儿》(2006)、《夜晚的沙滩》(2007)和散文、访谈集《不确定的碎片》(2003)。
说吧,那不勒斯
《巴黎评论》在2015年做埃莱娜·费兰特的访谈时,她说过这样一段话:费兰特将这些碎片串接起来,组成了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,乐声缭绕。
因为手边的这巴黎评论》特辑——女性作家访谈,在迪内森、波伏娃、毕肖普、尤瑟纳尔之后,访谈的第五位对象就是从不露面的,几近神秘的费兰特,于是我在之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,断断续续将厚厚四部发生在那不勒斯的故事读完,一千六百多页,跨越六十多年历史。可以说是相当顽强的记忆,刻骨铭心的人生,不可重来。
我没有选择看同名的电影,而是选择了阅读,因为费兰特的文字很倔强,心理描写多,细节丰富,处处可见的细腻的剖白,和粗粒的城市背景形成对比。
我愿意成为叙述的倾听者。
曾经在欧洲的列车上遇到过一位小伙子,湛蓝如海水的眼睛,颚下微微淡黄的细须,腼腆地说他是意大利人。我问他是做什么的,他笑盈盈答道:"我是做披萨的,现在回老家去。" 我很高兴他是做披萨的,随口问他老家在意大利哪里。他说了一个地名,我没听清,他便在谷歌地图上指给我看。"那里夏天很热,没有空调,我们天天去海里游泳,大海很凉,天空很高。" 我看了他在地图上点的意大利语地名 —— Napoli (拿波里)。之后我才知道,那个地名,英语叫 Naples(那不勒斯)。
那是我之一次见到一个那不勒斯人。他是做披萨的,非常好。
我知道,那不勒斯人通常说他们不是意大利人——因为,那不勒斯,是那么与众不同。
不少人会引用歌德赞美那不勒斯的那句名言: “朝见那不勒斯,夕死可矣!” (Siehe Neapel und stirb!)我直觉这应该不是歌德说话的腔调,于是特意去查了歌德的《意大利游记》(Italienische Reise)原文中的这段话。原来,歌德文中是援引了意大利诗人的话 "Vedi Napoli e poi muori!"
那不勒斯的自由与放纵,歌德在1786年就见识了。我不知他是否认同其引用的这句话,但确信歌德在那不勒斯海岸边的酒馆里,与人呼喝碰杯时,满面红光,操着意大利语致辞的,一定是这句话。
而我曾经邂逅的那位那不勒斯小伙,他描述的海边夏日,正符合我们想象中的那不勒斯:长时间的日照,持久的晴朗阳光。无处不在的教堂构造出魔幻的光影,转角可见的耶稣或圣玛丽像为人提供着指引。或者,如果我们读到加缪描写海边景象的句子,那将更令人心潮澎湃:
虽然歌德在那不勒斯享受着醉生梦死的时光,但在他酒醒之后,依然不忘持有上帝视角,来看待众生。难怪费兰特在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的扉页里,上来就搬出歌德《浮士德》中如下几句,以此来镇住四部长作:
埃莱娜·费兰特也是那不勒斯的吟唱者。
但我几乎可以想象,她会指着旅游杂志上的照片,抬眼看着你说:“不,亲爱的,这就是你们想要看到的吧?可惜不是。”
她用四部厚厚的书,几十个人物,横跨半个多世纪的纠缠,把游客和诗人们拽进她的城区, 那些弥漫着甜蜜、罪恶、爱恋、仇恨、宽容、嫉妒、细腻、粗糙的街道,那些充斥了所有人类情感的角落 。
果要用语言来描述费兰特笔下的那不勒斯,说说四部曲告诉了我们什么,你会发现自己表达的匮乏,或者是对表达的抵触。
你情愿那些还是碎片,散落在那不勒斯的街道各处,它们还不是曲子,你尚还可以一块块去捡拾,看它们光芒与黯淡的转化过程。 虽然你也可以用超越情节的方式来讲述,但那种可以预见的赘述,或者是咀嚼后的絮叨,显然不会令听者愉快。
费兰特应该是唯一的叙述者,其它人不是,包括读者。
倘若真要寻找一种表达方式,我更愿意借用伦敦摄影师 Bruce Gilden 的一组照片来解读那不勒斯。
初次看到这些照片,我觉得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里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走了出来。是的,没有比这些更让人震撼的了,这些照片无与伦比。
在Bruce Gilden 所有的照片中,我唯独无法选出与莉拉相符的一张。莉拉太复杂,她的复杂纠缠了整部小说,或者说是纠缠了整整半个多世纪的时空。一切都在迅速变化,一切都在急切地轮回。我很难在脑海中勾勒出莉拉的形象, 尽管叙述者埃莱娜始终在执着地刻画莉拉,但终究是一场持久的,如同抗争般的探究,没有终局。
与所有涉及两个主线人物的小说一样,我无法不产生将莉拉和埃莱娜视为同一个人的两面的念头。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,曾经也坚信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分身(黑塞《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》),而德米安与辛克莱也是(黑塞《德米安》),甚至可以说哈利波特与伏地魔也是。现在,我也如是看待莉拉和埃莱娜。 莉拉的身体里住着埃莱娜,埃莱娜的身体里住着莉拉。
直至读了《巴黎评论》,才看到费兰特精准地道出了所有人的感觉:
我不想勾勒莉拉的形象,也不想寻找类似于她的影像。发生了太多的事,岁月残酷如刀。我只想回到小说的最初,停留在文字中美好的一幕:
不得不说,费兰特在整部小说中尽量保持着叙述的语调,很少议论。若能耐心读到最后一部,即第四部《失踪的孩子》,你方能读到一些她想要告诉你的东西。
那不勒斯不仅仅是一座城市,而是一个宇宙 ,在这个宇宙中,万事万物都在轮回。那不勒斯用历史展现了从辉煌到沉沦,再从沉沦到辉煌,继而预备了下一次沉沦的过程。映射到人间,可以看到好人会变成恶人,继而又会变回好人。善成了恶,恶又回到了善。没有完全的善,也没有完全的恶。可以看出,费兰特避免用直白的方式表述这种宇宙观,最终却在第四部的一处,通过莉拉对伊玛讲的一段话,揭示出来:
没有人应该忘记,在那不勒斯湾,睡着维苏威火山,时刻提醒着人们: 再伟大的人类事业,那些最精美的作品,大火、地震、火山的灰烬还有大海,几秒时间就会让它们都化为乌有。
在这样一种悲观主义下,我们才能理解莉拉想要 “抹去” 自己所有痕迹的念头,和最终付诸的行动。莉拉想自我消失,埃莱娜阻止消失,她顽强地记录了莉娜,阻止记忆消失。
我更愿意相信, 费兰特想要竭力阻止的,是那不勒斯历史记忆的消失,是人类时空记忆的消失 。虽然在一切都在 “几秒时间就会化为乌有”(我们确信将来一定是如此),但留下文字是有意义的。 即便最后文字也没有意义了,但作家用文字做坚定表述的过程,依然意义非凡。
过去和现在的界限可以消失,将来可以化为乌有,但是爱,拒绝消失。
这就是我在这部书里读到的东西,费兰特也许说了,也许没说,但我想这样读。
维苏威火山在公元79年的爆发摧毁了庞贝城之后,又爆发了多次。一切都在摧毁和重来。之后的千百年,无数生命更替,出现并消亡。 “而孩子们死去,双眼深邃,他们一无所知,成长然后死去。而所有人走各自的路。”(霍夫曼斯塔尔)
而维苏威火山一直在那儿,那不勒斯城一直在那儿。
费兰特依然在顽强地讲述和记录着故土,一如她的祖先诗人们一样,他们是贺拉斯、维吉尔、奥维德。 记忆是与时间的抗争,所有的书写者,都在用文字,做着这件事 —— 书写永恒黑暗之间瞬息的生命之光,留住它。
我想,倘若有一天,费兰特对漫长的讲述感到疲惫了,她兴许会微笑着说:“好了,现在,那不勒斯,你自己说吧。”
如何评价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中,尼诺·萨拉托雷这个角色?
尼诺像是一个出口,一个从冷暗逼仄窒息的困境解脱出来,通向清新广阔自由的大世界的出口。只可惜这个出口并非一条康庄大道,这是一条蜿蜒阴湿令人作呕的地道,仅仅因为它跟明朗的外界相通,才拥有一些蛊惑人心的魅力。